●秦钠
2024年,为了筹备纪念费孝通先生田野调查90周年活动,应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的邀请,笔者随调研团一行踏上了大瑶山腹地。1935年,年仅25岁的费孝通先生就是沿着当时更为险峻的山路,携新婚妻子王同惠女士跋山涉水进入了这片神奇的土地,开启了一场中国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田野调查。
六巷村:学术生涯的起点
尽管盘山公路取代了当年费孝通夫妇跋涉的羊肠小道,但喀斯特地貌的陡峭山势依然令人望而生畏。踏入六巷村的那一刻,时光仿佛倒流。村口那棵百年古榕依然枝繁叶茂,树干上缠绕的红布条在微风中轻轻飘动。当地乡干部介绍说,“这是我们的神树。当年费孝通先生就在这棵树下为村民测量体质数据,开展体质人类学调查,王同惠进行社会组织调查。”这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一路走一路写,写出了《桂行通讯》,在《北平晨报》和天津《益世报》上连载,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《桂行通讯》中记录了费孝通夫妇“日食淡饭,夜卧土屋”,以及与瑶民围坐饮酒、猜拳,学说瑶话,为瑶民写生等饶有趣味的生活日常。
沿着石板路前行,传统的干栏式木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。这些以杉木为骨架、青瓦覆顶的建筑,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坚固如初。当地乡干部指着其中一栋说:“那就是费老当年住过的地方。”土黄色的外墙,木质框架,上层是当年费孝通夫妇居住的空间。寓所内保留了他们当年使用过的部分物品,有书桌、书籍、手稿等,展现了他们在大瑶山的生活和工作场景。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里,年轻的费孝通正在为瑶族老人测量头骨,王同惠则在一旁认真记录。照片中瑶族老人憨厚的笑容与学者专注的神情形成鲜明对比,却又显得如此和谐,这从一个侧面记录着他们与当地村民的深厚情谊。寓所的陈设简单而朴素,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。
六巷村费孝通纪念馆里,那张手绘的1935年考察路线图清晰显示:他们从柳州经象州进入大瑶山,在瑶族向导的指引下,先后走访六巷、门头、古陈等花篮瑶、坳瑶村寨。“他们白天做调查,晚上就着油灯整理资料。”“王先生(当地人对王同惠的尊称)总爱问瑶族服饰上刺绣图案的含义,一聊就是大半夜。”
在六巷村调查时,费孝通先生深入了解瑶族的“石牌制度”,即一种以石碑为载体,记录着乡规民约、维护社会秩序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。这种独特的制度引起了费孝通先生的浓厚兴趣,并成为他日后研究瑶族社会的重要切入点。石碑制起源于明代瑶族迁徙定居时期(15~16世纪),与瑶族《过山榜》等文献记载的自治传统一脉相承,清代嘉庆年间(1796~1820)形成完整制度体系,是瑶族社会长期沿袭的一种民间法律形式。核心内容是将村寨共同遵守的规约镌刻在石碑上,立于村寨的公共场所(如寨门、鼓楼旁),作为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。
如今六巷村的石碑制度已有形式上的变化,传统刻在的石碑上的规约内容改为“村规民约”宣传栏,或者电子公示(村委会LED屏)并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衔接。
门头村:永恒的爱情绝唱
告别六巷村,我们向更深处的门头村进发。山路愈发崎岖,车子不时会路过湍急的溪流。“当年可没有桥。”当地瑶族群众说,“费老他们得靠瑶民向导背着才能艰难地涉水渡过。”
门头村的费孝通社会调研旧址保存得更为完整。卧室里简陋的木床,诉说着那段艰苦而充实的调研岁月。墙上挂着一张特别的地图,上面用红笔标记着1935年12月16日那个改变一切的日子。“那天他们要去古陈屯。”当地瑶族群众的声音低沉下来。1935年12月16日,一场突如其来的山雨改变了一切。在古陈屯到罗运的山道上,费孝通和王同惠因迷路进入了竹林,费先生误踏捕虎陷阱,双腿被竹签刺穿,王同惠使出浑身力气推开石头,冒雨下山求救,却不幸跌入深渊。就这样,24岁的王同惠永远消失在了茫茫山林中。第二天,村民发现了身负重伤、奄奄一息的费先生,在村民的努力下才幸免于难!七天后,当身负重伤的费孝通看到放在大石头上的王同惠遗体时,他难掩悲痛挣脱别人的搀扶决意将头撞向大石头……幸好村民们早有防备,紧紧地按住了他,以后村里每天都派专人守护着。
王同惠的突然遇难,对费先生打击巨大。在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后记里他这样写道:“同惠死后,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,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,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,一直到现在,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!”当费孝通逐渐从痛苦中清醒过来,他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。“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,为学术服务了,因为她爱我,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。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,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《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》实现在这个世界上。”学术生涯意外遭受重创,费孝通仍然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和妻子年轻时的梦想,他以惊人的毅力,边养伤边顽强完成了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。最终成为了中国著名的人类学者、社会学家,为后来提出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”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走进门头村花蓝瑶博物馆,一套精美的瑶族传统服饰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深蓝的底色上,五彩丝线绣着繁复的图案。“这是新娘装。”讲解员小盘说,“王同惠先生曾详细记录过这些图案的象征意义。”在博物馆的角落里,发现了一本复制的田野笔记。娟秀的字迹记录着花蓝瑶妇女的日常生活:“晨起舂米,歌声与杵声相应和……”这是王同惠的手笔。透过这些文字,仿佛看见她蹲在火塘边,与瑶族妇女们说笑聊天的场景。
下古陈村:流芳亭前的沉思
午后,我们来到下古陈村。青山环抱中,一座四角亭静静伫立,这就是“王同惠流芳亭”。亭前的石碑上,“妻同惠”三个字笔力千钧,却又透着说不尽的哀思。“费老后来很少提起那天的经历,”当地村干部抚摸着石碑说,“但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上,这是对王同惠最好的纪念。”亭内挂着王同惠肖像,她年轻秀丽的脸庞上目光清澈而坚定。亭柱上刻着对联“淑德千年在,精神万古存”。流芳亭不仅是对王同惠女士的纪念,也是对那段艰苦而充满理想的学术岁月的缅怀。1985年,六巷村干部和群众集资修建了流芳亭,并立石碑纪念。每年清明,村民都会自发来此祭扫。“在我们瑶族人看来,她已经成为这座山的守护神了。”亭中常有游客驻足,感受这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与学术奉献精神。
沿着石阶来到下古陈村的黄泥鼓博物馆,我们见到了一种独特的乐器。鼓身用整段泡桐木镂空制成,鼓面蒙着发黄的山羊皮或黄牛皮,用竹钉固定。鼓身上涂抹了一种特制的黄泥浆(当地称为“泥膏”),并通过泥层厚度来调节音色,形成浑厚低沉的独特音效。“费老最早记录了黄泥鼓舞与瑶族祭祀的关系。”馆长介绍说,“现在它已经是国家级非遗了。”在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及相关笔记中,记录了包括黄泥鼓舞在内的瑶族传统祭祀文化。黄泥鼓舞起源于瑶族“盘王祭祀”仪式,是纪念始祖盘瓠的重要表现形式,具有娱神、祭祖、祈福等多重功能,在“盘王节”“度戒”等重大仪式中表演。
90年前费孝通先生的调查研究记录为研究瑶族原始宗教、艺术起源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,充分揭示了黄泥鼓舞与瑶族社会结构的深层关联。在费孝通的影响下,黄泥鼓舞逐渐从传统的祭祀活动走向国际舞台。1988年,黄泥鼓舞在北京惊艳亮相;1996年,古陈村黄泥鼓舞表演队远赴日本公演,将瑶族文化推向世界。
博物馆:学术精神的传承
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。走进“费孝通与王同惠瑶族调查专题展”的展厅,时间仿佛被折叠。玻璃展柜中泛黄的笔记本、已经褪色的老照片、略显粗糙的手绘地图,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,却承载着中国社会学、人类学史上的一段传奇。
展厅入口处复原了费孝通和王同惠两人当年居住的瑶族民居场景,粗糙的木桌上是他们使用过的煤油灯和钢笔;墙上悬挂着放大处理的田野照片,照片中瑶族群众的服饰细节清晰可见。展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王同惠的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瑶语词汇与汉语对照,字迹娟秀飘逸。
在费孝通专题展区,五张不同时期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:从1935年的青年学者,到1988年白发苍苍的学术泰斗,不变的是那双睿智的眼睛和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
“费老先后五次来到大瑶山。”讲解员说,“从最初的学术调查,到后来的扶贫建议,他始终惦记着大瑶山里的瑶族同胞。”
展柜里,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的手稿已经泛黄,但那些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依然熠熠生辉。旁边陈列着费老后来提出的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”理论著作,两条学术脉络在这里完美衔接。
暮色中,我们的车缓缓驶离大瑶山。回望渐行渐远的群山,我忽然明白,大瑶山田野调查是费老“从实求知”学术精神的典型写照。他与妻子王同惠扎根瑶寨,学习瑶语,参与瑶民日常生活。“参与式观察”使他能够透过表面现象,理解瑶族社会的内在组织逻辑。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怀贯穿其学术生涯,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实践的重要起点。通过深入考察瑶族社会结构、文化习俗及其与汉族的互动关系,揭示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文化的共存逻辑。不同民族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,通过经济互补、社会交往形成有机整体,为“多元一体”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,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启示。大瑶山上费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成果,更是一种治学精神:扎根泥土,尊重文化,用生命做学问。
在大瑶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,学术与生命、历史与现实、汉族与瑶族,早已水乳交融。而费孝通与王同惠的故事,将随着大瑶山的云雾和溪涧清澈的山水永远流传下去。
(作者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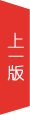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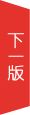


 前一期
前一期